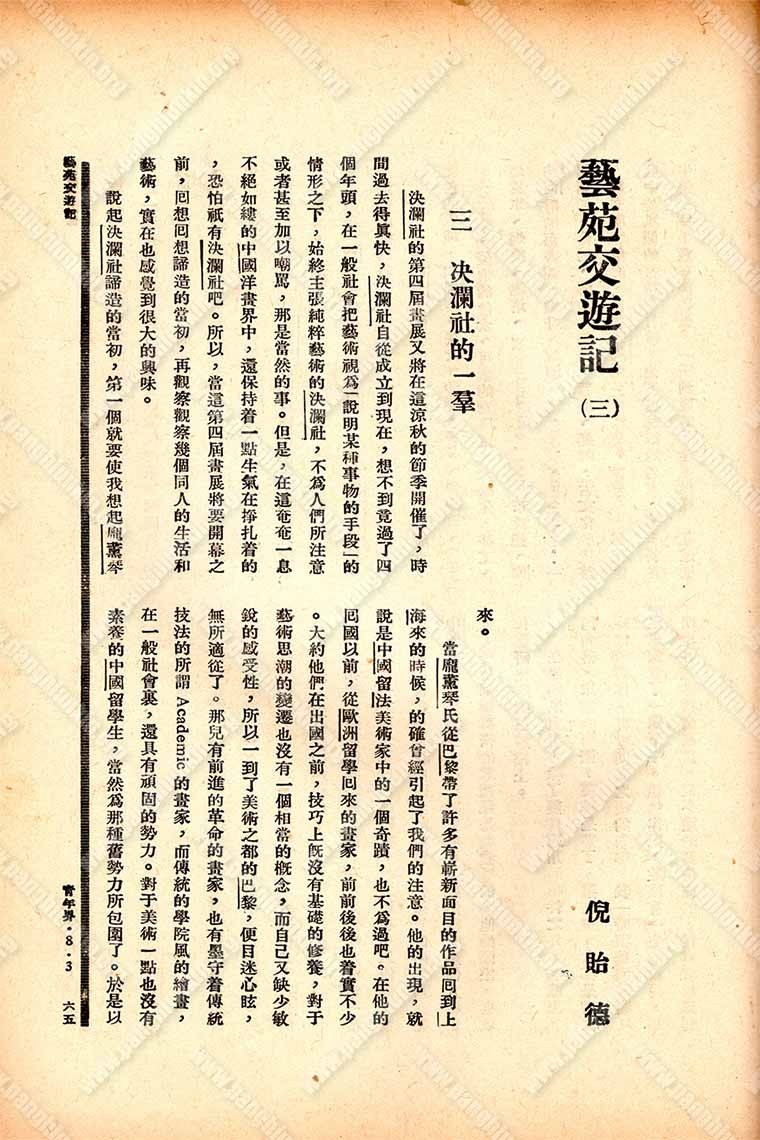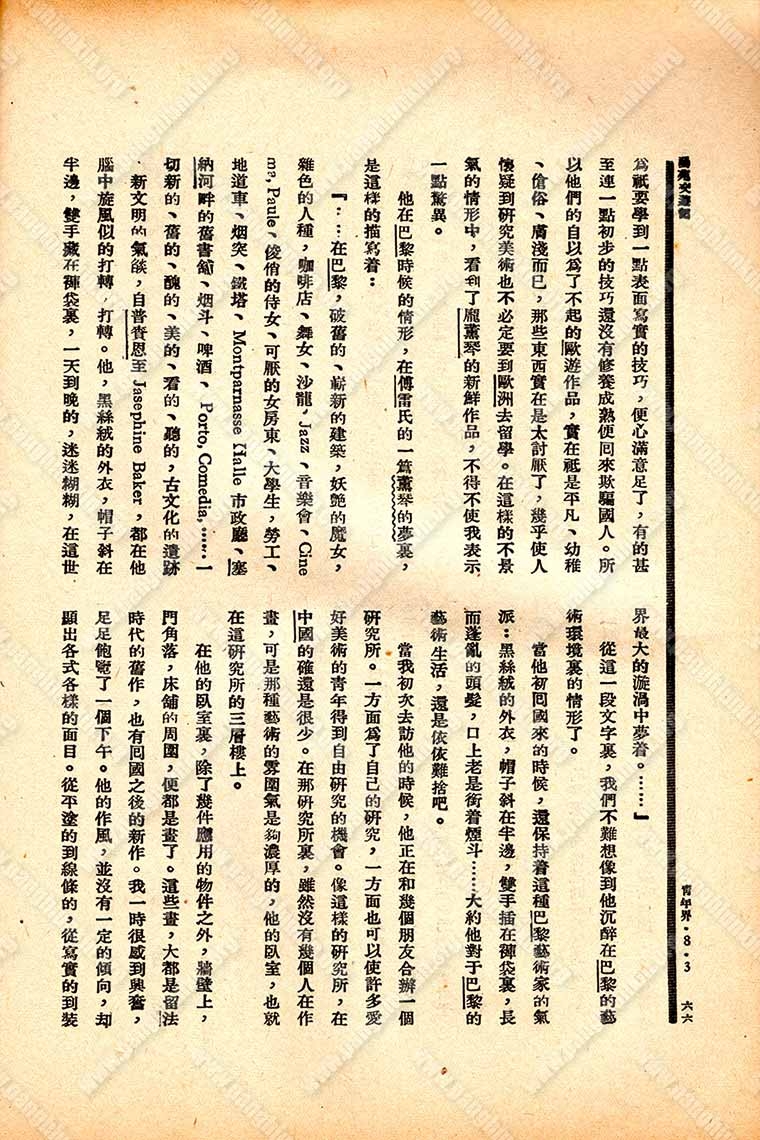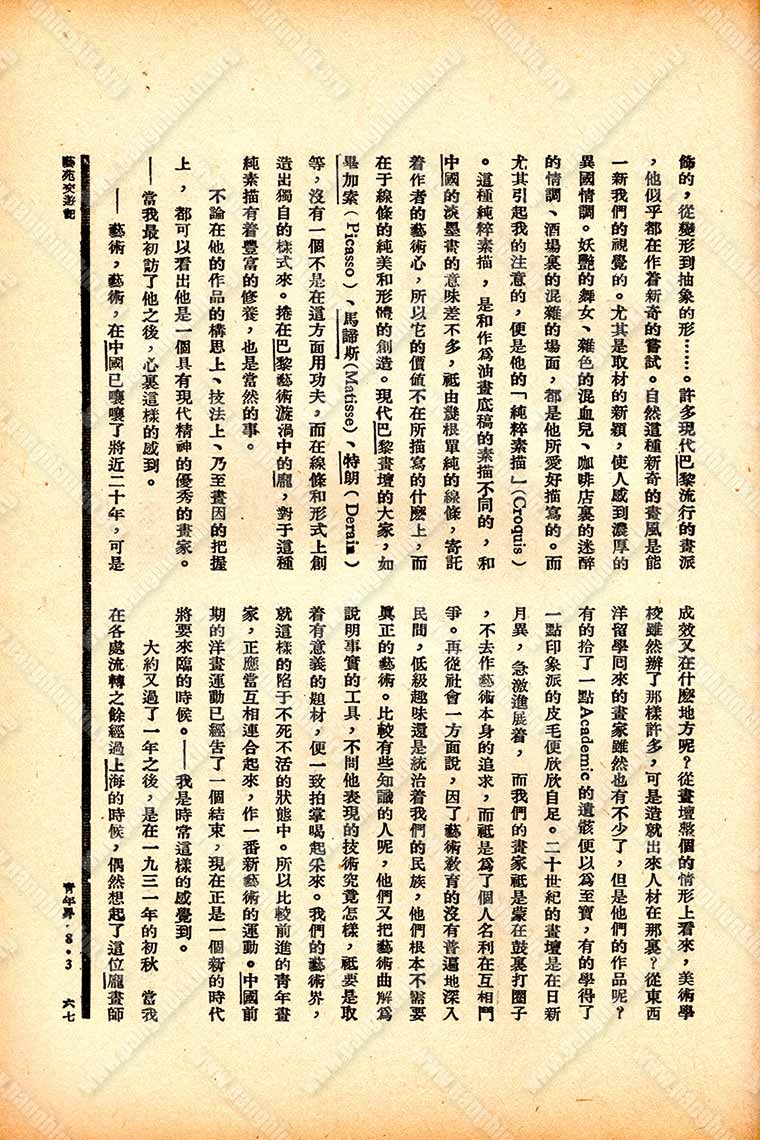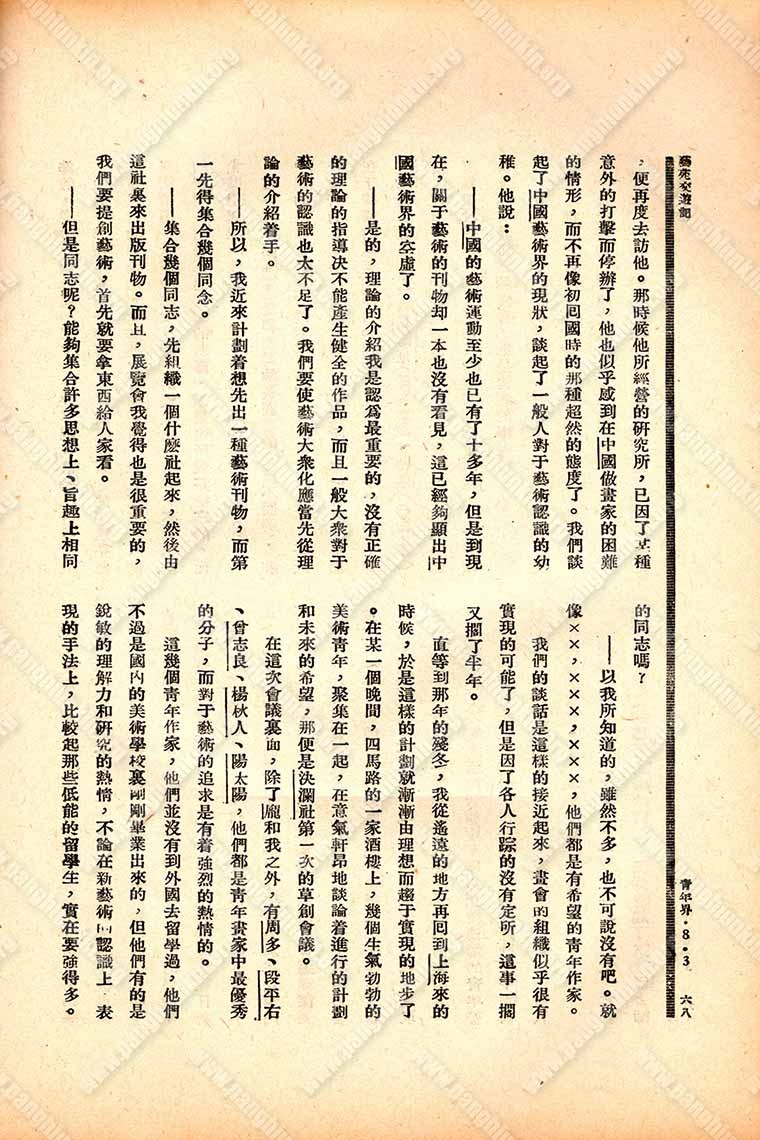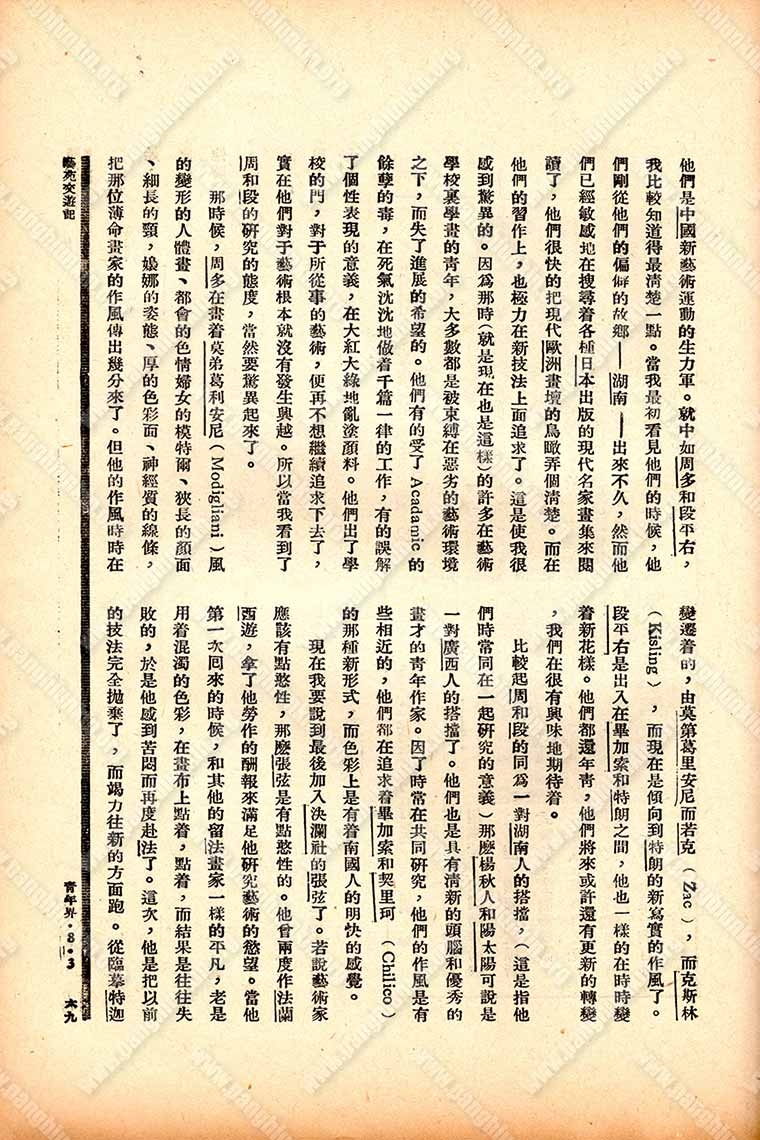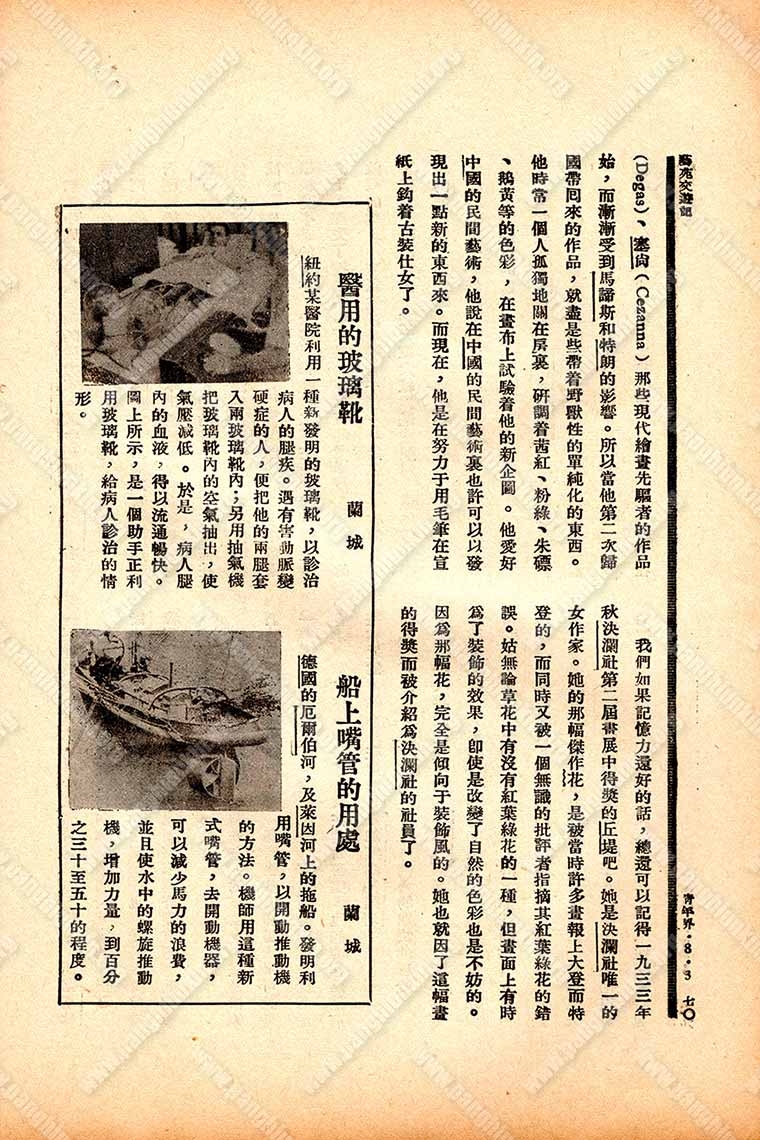三 決瀾社的一群
決瀾社的第四屆畫展又將在這涼秋的季節開催了,時間過去得真快,決瀾社自從成立到現在,想不到竟過了四個年頭,在一般社會把藝術視為「說明某種事物的手段」的情形之下,始終主張純粹藝術的決瀾社,不為人們所注意或者甚至加以嘲罵,那是當然的事。但是,在這奄奄一息不絕如縷的中國洋畫界中,還保持著一點生氣在掙扎著的,恐怕只有決瀾社吧。所以,當這第四屆畫展將要開幕之前,回想回想諦造的當初,再觀察觀察幾個同人的生活和藝術,實在也感覺到很大的興味。
說起決瀾社諦造的當初,第一個就要使我想起龎薰琹來。
當龎薰琹氏從巴黎帶了許多有嶄新面目的作品回到上海來的時候,的確曾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的出現,就說是中國留法美術家中的一個奇蹟,也不為過吧。在他的回國以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畫家,前前後後也著實不少。大約他們在出國之前,技巧上既沒有基礎的修養,對於藝術思潮的變遷也沒有一個相當的概念,而自己有缺少敏銳的感受性,所以一到了美術之都的巴黎,便目迷心眩,無所適從了。那兒有前進的革命的畫家,也有墨守著傳統技法的所謂Academic的畫家,而傳統的學院風的繪畫,在一般社會裡,還具有頑固的勢力。對於美術一點也沒有素養的中國留學生,當然為那種舊勢力所包圍了。於是以為只要學到一點表面寫實的技巧,便心滿意足了,有的甚至連一點初步的技巧還沒有修養成熟便回來欺騙國人。所以他們的自以為了不起的歐遊作品,實在只是平凡、幼稚、傖俗、膚淺而已,那東西實在是太討厭了,幾乎使人懷疑到研究美術也不必定要到歐洲去留學。在這樣的不景氣的情形中,看到了龎薰琹的新鮮作品,不得不使我表示一點驚異。
當龎薰琹氏從巴黎帶了許多有嶄新面目的作品回到上海來的時候,的確曾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他的出現,就說是中國留法美術家中的一個奇蹟,也不為過吧。在他的回國以前,從歐洲留學回來的畫家,前前後後也著實不少。大約他們在出國之前,技巧上既沒有基礎的修養,對於藝術思潮的變遷也沒有一個相當的概念,而自己又缺少敏銳的感受性,所以一到了美術之都的巴黎,便目迷心眩,無所適從了。那兒有前進的革命的畫家,也有墨守著傳統技法的所謂 Academic 的畫家,而傳統的學院風的繪畫,在一般社會裡,還具有頑固的勢力。對於美術一點也沒有素養的中國留學生,當然為那種舊勢力所包圍了。於是以為只要學到一點表面寫實的技巧,便心滿意足了,有的甚至連一點初步的技巧還沒有修養成熟便回來欺騙國人。所以他們的自以為了不起的歐遊作品,實在只是平凡、幼稚、傖俗、膚淺而已,那些東西實在是太討厭了,幾乎使人懷疑到研究美術也不必定要到歐洲去留學。在這樣的不景氣的情形中,看到了龎薰琹的新鮮作品,不得不使我表示一點驚異。
他在巴黎時候的情形,在傅雷氏的一篇薰琹的夢裡,是這樣的描寫著:
「⋯⋯在巴黎,破舊的、嶄新的建築,妖豔的魔女,雜色的人種,咖啡店、舞女、沙龍、Jazz、音樂會、Cinema,Paule、俊俏的侍女、可厭的女房東、大學生,勞工、地道車、煙突、鐵塔、Montparnasse Halle 市政廳、塞納河畔的舊書鋪、煙斗、啤酒、Porto,Comedia,⋯⋯一切新的、舊的、醜的、美的、看的、聽的,古文化的遺跡,新文明的氣焰,自普賚恩至 Josephine Baker,都在他腦中旋風似的打轉,打轉。他,黑絲絨的外衣,帽子斜在半邊,雙手藏在褲袋裡,一天到晚的,迷迷糊糊,在這世界最大的漩渦中夢著。⋯⋯」
從這一段文字裡,我們不難想像到他沉醉在巴黎的藝術環境裡的情形了。
當他初回國來的時候,還保持著這種巴黎藝術家的氣派:黑絲絨的外衣,帽子斜在半邊,雙手插在褲袋裡,長而蓬亂的頭髮,口上老是銜著煙斗⋯⋯大約他對於巴黎的藝術生活,還是依依難捨吧。
當我初次去訪他的時候,他正在和幾個朋友合辦一個研究所。一方面為了自己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使許多愛好美術的青年得到自由研究的機會。像這樣的研究所,在中國的確還是很少。在那研究所裡,雖然沒有幾個人在作畫,可是那種藝術的氛圍氣是夠濃厚的,他的臥室,也就在這研究所的三層樓上。
在他的臥室裡,除了幾件應用的物件之外,牆壁上,門角落,床鋪的周圍,便都是畫了。這些畫,大都是留法時代的舊作,也有回國之後的新作。我一時很感到興奮,足足飽覽了一個下午。他的作風,並沒有一定的傾向,卻顯出各式各樣的面目。從平塗的到線條的,從寫實的到裝飾的,從變形到抽象的形⋯⋯。許多現代巴黎流行的畫派,他似乎都在作著新奇的嘗試。自然這種新奇的畫風是能一新我們的視覺的。尤其是取材的新穎,使人感到濃厚的異國情調。妖豔的舞女、雜色的混血兒、咖啡店裡的迷醉的情調、酒場裡的混雜的場面,都是他所愛好描寫的。而尤其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他的「純粹素描」(Croquis)。這種純粹素描,是和作為油畫底稿的素描不同的,和中國的淡墨畫的意味差不多,只由幾根單純的線條,寄託著作者的藝術心,所以它的價值不在所描寫的什麼上,而在於線條的純美和形體的創造。現代巴黎畫壇的大家,如畢加索(Picasso)、馬諦斯(Matisse)、特朗(Derain)等,沒有一個不是在這方面用功夫,而在線條和形式上創造出獨自的樣式來。捲在巴黎藝術漩渦中的龎,對於這種純素描有著豐富的修養,也是當然的事。
不論在他的作品的構思上、技法上、乃至畫因的把握上,都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具有現代精神的優秀的畫家。——當我最初訪了他之後,心裡這樣的感到。
——藝術,藝術,在中國已嚷嚷了將近二十年,可是成效又在什麼地方呢?從畫壇整個的情形上看來,美術學校雖然辦了那樣許多,可是造就出來人材在那裡?從東西洋留學回來的畫家雖然也有不少了,但是他們的作品呢?有的拾了一點 Academic 的遺骸便以為至寶,有的學得了一點印象派的皮毛便欣欣自足。二十世紀的畫壇是在日新月異,急激進展著,而我們的畫家只是蒙在鼓裡打圈子,不去作藝術本身的追求,而只是為了個人名利在互相鬥爭。再從社會一方面說,因了藝術教育的沒有普遍地深入民間,低級趣味還是統治著我們的民族,他們根本不需要真正的藝術。比較有些知識的人呢,他們又把藝術曲解為說明事實的工具,不問他表現的技術究竟怎樣,只要是取著有意義的題材,便一致拍掌喝起采來。我們的藝術界,就這樣的陷於不死不活的狀態中。所以比較前進的青年畫家,正應當互相連合起來,作一番新藝術的運動。中國前期的洋畫運動已經告了一個結束,現在正是一個新的時代將要來臨的時候。——我是時常這樣的感覺到。
大約又過了一年之後,是在一九三一年的初秋,當我在各處流轉之餘經過上海的時候,偶然想起了這位龎畫師,便再度去訪他。那時候他所經營的研究所,已因了某種意外的打擊而停辦了,他也似乎感到在中國做畫家的困難的情形,而不再像初回國時的那種超然的態度了。我們談起了中國藝術界的現狀,談起了一般人對於藝術認識的幼稚。他說:
——中國的藝術運動至少也已有了十多年,但是到現在,關於藝術的刊物卻一本也沒有看見,這已經夠顯出中國藝術界的空虛了。
——是的,理論的介紹我是認為最重要的,沒有正確的理論的指導決不能產生健全的作品,而且一般大眾對於藝術的認識也太不足了。我們要使藝術大眾化應當先從理論的介紹著手。
——所以,我近來計畫著想先出一種藝術刊物,而第一先得集合幾個同志。
——集合幾個同志,先組織一個什麼社起來,然後由這社裡來出版刊物。而且,展覽會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提創藝術,首先就要拿東西給人家看。
——但是同志呢?能夠集合許多思想上、旨趣上相同的同志嗎?
——以我所知道的,雖然不多,也不可說沒有吧。就像××,×××,×××,他們都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我們的談話是這樣的接近起來,畫會的組織似乎很有實現的可能了,但是因了個人行踪的沒有定所,這事一擱又擱了半年。
直等到那年的殘冬,我從遙遠的地方再回到上海來的時候,於是這樣的計劃就漸漸由理想而趨於實現的地步了。在某一個晚間,四馬路的一家酒樓上,幾個生氣勃勃的美術青年,聚集在一起,在意氣軒昂地談論著進行的計劃和未來的希望,那便是決瀾社第一次的草創會議。
在這次會議裡面,除了龎和我之外,有周多、段平右、曾志良、楊秋人、陽太陽,他們都是青年畫家中最優秀的分子,而對於藝術的追求是有著強烈的熱情的。
這幾個青年作家,他們並沒有到外國去留學過,他們不過是國內的美術學校裡剛剛畢業出來的,但他們有的是銳敏的理解力和研究的熱情,不論在新藝術的認識上,表現的手法上,比較起那些低能的留學生,實在要強得多。他們是中國新藝術運動的生力軍。就中如周多和段平右,我比較知道得最清楚一點。當我最初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剛從他們的偏僻的故鄉——湖南——出來不久,然而他們已經敏感地在搜尋著各種日本出版的現代名家畫集來閱讀了,他們很快地把現代歐洲畫壇的鳥瞰弄個清楚。而在他們的習作上,也極力在新技法上面追求了。這是使我很感到驚異的。因為那時(就是現在也是這樣)的許多在藝術學校裡學畫的青年,大多數都是被束縛在惡劣的藝術環境之下,而失了進展的希望的。他們有的受了 Academic 的餘孽的毒,在死氣沈沈地做著千篇一律的工作,有的誤解了個性表現的意義,在大紅大綠地亂塗顏料。他們出了學校的門,對於所從事的藝術,便再不想繼續追求下去了,實在他們對於藝術根本就沒有發生興趣。所以當我看到了周和段的研究的態度,當然要驚異起來了。
那時候,周多在畫著莫弟葛利安尼(Modigliani)風的變形的人體畫、都會的色情婦女的模特爾、狹長的顏面、細長的頸,嬝娜的姿態、厚的色彩面、神經質的線條,把那位薄命畫家的作風傳出幾分來了。但他的作風時時在變遷著的,由莫第葛里安尼而若克(Zac),而克斯林(Kisling),而現在是傾向到特朗的新寫實的作風了。段平右是出入在畢加索和特朗之間,他也一樣的在時時變著新花樣。他們都還年青,他們將來或許還有更新的轉變,我們在很有興味地期待著。
比較起周和段的同為一對湖南人的搭擋,(這是指他們時常同在一起研究的意義)那麼楊秋人和陽太陽可說是一對廣西人的搭擋了。他們也是具有清新的頭腦和優秀的畫才的青年作家。因了時常在共同研究,他們的作風是有些相近的,他們都在追求著畢加索和契里珂(Chilico)的那種新形式,而色彩上是有著南國人的明快的感覺。
現在我要說到最後加入決瀾社的張弦了。若說藝術家應該有點憨性,那麼張弦是有點憨性的。他曾兩度作法蘭西遊,拿了他勞作的酬報來滿足他研究藝術的慾望。當他第一次回來的時候,和其他的留法畫家一樣的平凡,老是用著混濁的色彩,在畫布上點著,點著,而結果是往往失敗的,於是他感到苦悶而再度赴法了。這次,他是把以前的技法完全拋棄了,而竭力往新的方面跑。從臨摹特迦(Degas)、塞尚(Cezanne)那些現代繪畫先驅者的作品始,而漸漸受到馬諦斯和特朗的影響。所以當他第二次歸國帶回來的作品,就盡是些帶著野獸性的單純化的東西。他時常一個人孤獨地關在房裡,研調著茜紅、粉綠、朱磦、鵝黃等的色彩,在畫布上試驗著他的新企圖。他愛好中國的民間藝術,他說在中國的民間藝術裡也許可以以發現出一點新的東西來。而現在,他是在努力於用毛筆在宣紙上鉤著古裝仕女了。
我們如果記憶力還好的話,總還可以記得一九三三年秋決瀾社第二屆畫展中得獎的丘堤吧。她是決瀾社唯一的女作家。她的那幅傑作花,是被當時許多畫報上大登而特登的,而同時又被一個無識的批評者指摘其紅葉綠花的錯誤。姑無論草花中有沒有紅葉綠花的一種,但畫面上有時為了裝飾的效果,即使是改變了自然的色彩也是不妨的。因為那幅花,完全是傾向於裝飾風的。她也就因了這幅畫的得獎而被介紹為決瀾社的社員了。